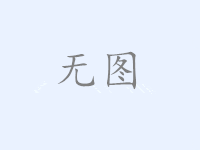事件复盘怎么做从“等待被爱”到“制定规则”:如何书写cos委托的女性叙事 稿件复盘
cos委托是基于二次元文化“cosplay”(角色扮演)的衍生服务,客户付费聘请coser扮演指定角色,提供线下陪伴、互动和拍摄等服务。花钱购买服务的客户被称为“单主”,进行角色扮演的coser被称为“委托老师”。值得注意的是,cos委托一般发生在女性与女性之间。
cos委托业务随着近年来国内乙女游戏(简称“乙游”)的兴起而发展。乙游是以女性玩家为主要受众、围绕一个女主人公和多个男性角色展开剧情的互动游戏。2017年,国内第一款乙游《恋与制作人》诞生。随后几年,《未定事件簿》《时空中的绘旅人》《光与夜之恋》《恋与深空》等乙游陆续问世。伽马数据发布的《2025中国游戏产业趋势及潜力分析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女性玩家在游戏市场规模同比增长124.1%,《光与夜之恋》等作品凭借沉浸式恋爱叙事吸引了90%的女性用户。越来越多年轻女性渴望将二次元的爱欲投射到现实世界,与虚拟角色建立真实的情感链接,于是,cos委托业务应运而生。
随着cos委托逐渐走入大众视野,委托服务的内容也不再局限于“乙游男主”的爱情主题委托,“姐姐委托”“妈妈委托”等亲情主题的cos委托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也拥有越来越高的浏览量。
深度训练营收集了近一年与cos委托主题相关的新闻报道、非虚构作品,从中选取了两篇进行分析,分别是【正面连接】刘诗予的和【Vista看天下】李彤的。我们希望通过与两位作者交流,更好地搭建起大众和cos委托背后的女性们的连接,让她们的情感需求和心理机制得以被看见。
无论是乙游玩家对理想恋爱关系的追求,还是缺乏原生家庭关爱的孩子对温暖母爱的向往,他们不再执着于“必须真实”,而是通过cos委托在角色扮演中寻找自己想要的爱。
正面连接的选题源于作者刘诗予对乙游玩家的长期观察。早在2017年12月,《恋与制作人》的上线就引起了刘诗予的关注和参与。2023年5月,【跳进兔子洞】播客推出节目《关于「一日男友」的幻想、沉迷和破灭》,介绍了cos委托的由来与基本概念。2024年2月,刘诗予听完这期播客后,发现cos委托背后有着复杂的情感维度,于是申报了这个选题,经过她三个月的采访写作,文章于5月20日发布,使更多人了解女性情感需求。
在操作选题与深入了解乙游玩家的过程中,刘诗予还亲自体验了一次cos委托,她明白cos委托不仅仅是简单的角色扮演,更是女性内心深处对“被尊重、被理解、被倾听”的情感需求的强烈投射。乙游的出现,为女性构建了一个浪漫又美好的乌托邦,她们能够在这里体验到理想的情感关系,获得情感上的慰藉。
《看天下》杂志2025年1月28日的封面故事以亲子关系为主题,是其中一篇,这一选题来源于李彤对年轻人迫切弥补家庭情感空缺这一社会现象的持续关注。李彤梳理近十年亲缘关系的演变发现:2008年豆瓣出现“父母皆祸害”小组(该小组已被关闭),组员们在其中讨论原生家庭、父母意志对于自己造成的伤害;2017年,这类吐槽小组消失后,“原生家庭”概念进入公共讨论视野。李彤认为这一概念的出现,显示出这代年轻人想试图超越吐槽本身,并去找到更多属于自己的力量。
2023年12月,凤凰网发布文章,讲述一位青年艺术家邹雅琦在网上不断招募有生育经验的人演她妈妈,去塑造一个她心目中理想的妈妈形象。2024年,“电子父母”引起了社交媒体上年轻人的广泛关注,他们试图从陌生人那里获取理想中的父爱和母爱。2024年9月,谷雨实验室的文章以自述形式呈现了妈妈委托这一现象。在这些报道之后,《看天下》试图回答未被充分讨论的问题,正如杂志封面标题所问:“亲情可以被替代吗?”当母爱成为可以购买的服务,我们每个人该如何重建真实的情感联结?
从“断亲”到“电子父母”,再到当下的妈妈委托服务,这些现象背后共同指向的是年轻人对获得更多被爱体验的渴望。年轻人渴望被爱,也拥有重建自我的勇气,他们尝试以各种方式获取情感支撑,努力寻找情感归宿。
在一些网络平台中,人们对委托行为的认识存在不同评价。有部分网友认为沉迷男友委托的女性群体是在“消费恋爱”或是寻求“情感替代”;且对约妈妈委托的单主形成了“缺爱”“逃避现实”的刻板印象。两篇文章通过描写单主和委托老师们的真实故事,呈现cos委托背后的复杂情感动机,打破大众偏见,展现女性通过委托服务实现自我探索与情感解放。
作者着墨最多的人物“甜甜”是一位已婚女性,但她依然会定期约男友委托。“甜甜在现实生活中拥有着没有矛盾的、和谐的、美满的婚姻,但不意味她只需要在这一个人身上获得所有的情感支持,这并不是她情感世界的全部。”刘诗予说道。
刘诗予在文章中使用“甜甜”的故事并非为了证明“婚姻不幸福才寻求虚拟慰藉”,也不是狭隘地论断现实婚姻、乙游男主或cos委托哪个更好,而是想要人们去理解为什么一个人身上可以同时出现丰富的需求。这篇文章展现了女性情感世界的广袤——她对浪漫的渴望、对角色扮演中沉浸式体验的享受,甚至是某种自我投射的愉悦。刘诗予认为,女性的情感需求在于她的心愿能够被理解,这种理解中包含着一个主体对另一个主体的尊重与珍视。因为这种理解难以在现实中得到满足,所以她们转而诉诸二次元的乙游和cos委托。
相较于男友委托的浪漫化叙事,妈妈委托的单主会向委托老师倾诉自己与母亲之间的创伤记忆。“在采访前我以为会比较难让受访者坦诚说出自己的经历,因为这会涉及到一些自己比较痛苦的回忆,比如妈妈去世、母女关系紧张等。但是在对话的过程中,我发现她们自己是愿意跟别人倾诉的。”李彤说道。约妈妈委托这种行为并不意味着女孩们“沉溺于过去”,相反,她们的坦诚恰恰是一种面对与疗愈。
《里单主冯曼与“妈妈”杨夕有两次委托服务:第一次委托中,杨夕扮演冯曼的妈妈,去弥补冯曼因为失去母亲而产生的遗憾;而在第二次委托时,冯曼去到了杨夕的家乡,想更加了解杨夕本人。李彤在对话中特地问其原因,冯曼回答道,妈妈去世已经成为既定事实,委托服务已经弥补自己在妈妈身上的遗憾,但仍然希望能有“妈妈”在自己身边的感觉。
部分人会认为妈妈委托是“替代母爱”的行为,“其实她们需要的是精神寄托,也就是母亲这个角色,母亲这个角色的意义可能会大于自己的亲生妈妈。”李彤谈道,她们非常清楚自己就是在拿钱购买母爱,她们知道现在需要的是什么,也知道妈妈委托不能替代自己真正的妈妈,然而在委托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温暖,能够给予她们继续生活的力量。
在这篇文章中,刘诗予有多重的视角和身份:她是乙游玩家,是cos委托的参与者,也是文章的写作对象。“因为和文中的女孩们有过类似的经历和经验,我更能够和她们共情。通过写作,我可以成为读者的眼睛,用一种和cos委托的女孩们更接近、更理解的视角去看待她们,并把它表达给外部对此完全陌生的人。”
在单主、委托老师这些女孩们和大众读者之间建立连接,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很多读者并不知道cos委托这种小众文化和领域,于是文章的第一部分「手机里的他」就介绍了:乙游是什么、cos委托是什么、乙游中的男主是什么样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写作,刘诗予也去体验了一次cos委托。让她没想到的是,她完全无法像她的采访对象那样享受其中,并且把眼前的coser带入成乙游里自己喜欢的角色。由此,「bug」和「梦的能力」这两部分浮现而出。许多约cos委托的女孩可以“梦”,是因为她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只是一场表演;而刘诗予“梦不了”,是她真的抱有一种期待,期待自己喜欢的乙游男主能完全出现在coser的身上。
“梦”的能力也是cos委托心理机制中最重要、最复杂的一环,反映了女孩们庞大的情感需求。她们在三次元失望后,转而向二次元寻觅理想的爱,那种爱强烈又真实,以至于她们希望在现实见到一个二次元的人。“梦”甚至是女孩们基于这样庞大的情感需求的一种“自我欺骗”——女孩们基于自己强烈的情感需求,让自己去相信明知不是事实的事实。她们如此渴望一段能被尊重、被看见、被理解的感情,以至于她们可以完成这种欺骗,说服自己——我真的和我喜欢的游戏里的男孩度过了美好的一天。
「爱是什么」和「爱他,还是爱她」两个章节,清晰呈现了对女孩们心理动机的剖析,文章的情感浓度也达到高潮。不同于前文从单主的视角展开叙述,这两个章节中委托老师的视角被补充进来。单主和委托老师互相给对方准备惊喜、委托老师会心疼有过抑郁症的单主、单主在约会时对委托老师无微不至的照顾……大量场景和细节向读者展示:cos委托不只是一场情感商品化的服务,它是一场由单主和委托老师共同编织的梦。一方面,文章需要通过丰富的故事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另一方面,文章也需要从具体的故事中抽象出人物的内心,让读者更好理解cos委托背后的情感机制。就像文章中写道:“在cos委托里,这些女孩们好像第一次发现,被看见、被夸奖、被包容,也可以是一种天然降临在自己身上的体验,不需要努力争取,不需要怀疑自己是否值得。”
在这篇文章中,李彤通过多方视角和正反面素材的选择和呈现,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关于妈妈委托的全景图。
妈妈委托产生的原因不能被简单概括为一种,事件的亲历者们各有各的理由。团子在原生家庭的妈妈那里无法得到爱,冯曼失去了妈妈——她们正好反映了妈妈委托中两类不同单主的需求。如果按照典型的“现象——原因”结构成文,一方面无法处理团子、冯曼、杨夕几人差异较大的不同视角,另一方面无法完整呈现妈妈委托背后的原因。李彤最终选择在文章的前两章分开讲述单主冯曼和团子两人的故事和进行妈妈委托的原因,其中第一章「再见妈妈」描写冯曼和杨夕,第二章「我想体验正常的母爱」描写团子和燕子阿姨。
无论是冯曼和杨夕的故事,还是团子和燕子阿姨的故事,都呈现出一种美好、理想、感人至深的状态——“女儿”们在委托中收获到理解、支持和爱,“妈妈”们也在这样的相处中获得治愈。但是这其实不是妈妈委托的全部。李彤认为,如果只从一个方面出发,不呈现一些争议和讨论,这篇文章所讲述的妈妈委托似乎就成为一个绝对好的事情,也就失去了做这个选题的意义。
第三章「月光曾照在我身上」探讨了妈妈委托中存在的争议和问题、以及它能否代替真正的母爱。“冯曼和团子在‘委托妈妈’身上体验了爱和温柔,但这并非全部。‘委托妈妈’终究是亲情的替代品,它需要理清边界,也存在着一定风险……还有一些哪怕竭尽全力也做不到的事。”博溪按照单主的要求还原其亲生妈妈并情景重现母女之间的一次争吵,这段经历带给她“不应该编造亲妈的立场去欺骗单主”的争议,还有过度陷入角色的心理伤害。妈妈辈的女性想去关心在母女关系中有遗憾的年轻女孩,但抛出去的真心可能被辜负,自己在进行角色扮演时,也可能受到伤害——这是隐藏在妈妈委托这一看似美好和感人的事物下的暗面。
Q:我们认为文章不仅打破了“女性等待被爱”的传统叙事,还展现女性作为情感规则制定者的主体性,这是否是您想表达的?
A:我们筹备时的核心问题,就是女性叙事和男性叙事的区别。在报题的前一两个月,男性向Galgame《完蛋,我被美女包围了》非常流行。在游戏里,女性角色不仅会迅速爱上男性玩家,情感发展过程也常被简略处理,这种男性叙事中呈现的更多是一种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而cos委托背后的乙游价值观并不是这样。
在女性理解的浪漫叙事和情感叙事里,乙游和cos委托的特殊性在于:她们更在意“两个人为什么相爱”,即“你是怎么爱上我的”、“我们的感情是如何产生的”。这种叙事强调在相爱的过程中双方持续的尊重、看见、理解与倾听,本质上呈现的是两个主体之间建立的亲密深度连接。这种关系建构会帮助女性建立自我认知——让女孩更清晰“我是谁”“我要的是什么”“什么会让我快乐”并勇于追求这种认知;同时也确立了一种平等范式——当你在追求自我存在与快乐时,并不需要通过贬低另一个主体来实现,而是维系着彼此尊重的对等关系。这两个主体之间建立的理想化的关系和平等的、相互包容的互动,恰恰是当下三次元异性恋中比较难充分实现的。
Q:在您的多篇文章里,您的视角、思考跟生活经历一直都是文章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您也提到过“写作最终会回到我的生命经验”,您的创作是否有一个母题?
A:我觉得它不能被概括为一个确定的母题。比如说,当一个人想要写作时,一定是这个人具有创造性,他的内心有想要吐露和对外表达、输出的东西。当人产生表达欲的时刻,根源必定在于存在强烈的倾诉欲望,那些真正吸引我的选题,本质上都具备某种触动我的力量,这种触动激发的表达欲有很多时候可能与你在世界上所关注的公共议题有关,也有可能是在自己的生命经验里那些未被解决的困惑,那些未被充分看见的问题的追问。
对我而言,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写作必定始于自我触动,唯有如此才能在文字与读者之间搭建情感共鸣。这种共鸣的重要性在于,它往往通过与自身生命经验的某种契合,或是与当下困惑的深层呼应得以建立。当然这绝非唯一路径,其他创作者也必然存在着属于他们的共鸣构建方式。
Q:妈妈委托提供了一种情感弥补的途径,您觉得还有哪些方式可以帮助在原生家庭中缺爱的人弥补情感上的缺失?
A:心理学知识还是挺有用的。“团子”后期自学了很多比较专业的心理学知识,她觉得通过学习这类知识能够帮助她更清晰地理解自我与原生家庭的关系状态。我记得豆瓣上有些书可以自主研究学习,例如:《突围原生家庭:如何在过去的伤痛中重建自我》。
我采访过的专家提出一个可以帮助改善家庭沟通的方法:如果每次口头与父母交流都会引发争吵,可以尝试转换沟通媒介,通过写信表达需求。这种书面形式往往能让诉求更温和,父母也更容易耐心理解。还有近期流行的“重新养育自己”,例如购买心仪物品、主动弥补童年遗憾等具象化行为来进行自我疗愈。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